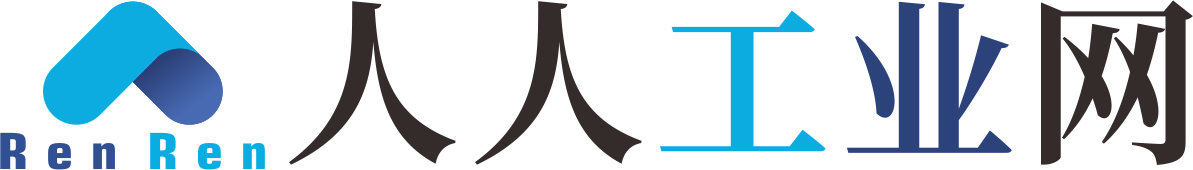即时焦点:私家车与中产:自由、便利,还是面子?
▲北京国贸CBD晚高峰的车流 图/视觉中国
 【资料图】
【资料图】
多年来,学者张珺目睹不少人在买车方面受到的“同辈压力”,汽车不仅成为他们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必要出行工具,同时成为他们传递财富、地位或身份认同的媒介。
私家车的普及表明,虽然轿车仍是确认个人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标志,但人们对于拥有轿车的愿望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工具性的,目的是获得社会地位”。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购车考量中都很看重家庭需求,只不过在表述上很不一样。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吴俊燊记者 欧阳诗蕾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从香港城市大学到张珺居住的港岛大约十公里。在每天的通勤路上,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系助理教授张珺选择坐四十分钟左右的地铁,尽管她曾做过长达十年的私家车研究。2023年出版的《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是她当年的研究成果。她以私家车为切入点,探究新世纪以来汽车消费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观念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生于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中产人士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命经验。
人们对汽车的理解随时代发生着变化——1990年代,汽车不仅代表着移动上的便利和自由,也承载着消费者对现代化的理想生活的向往。而现在,交通拥堵却成为了城市生活的常态。在张珺看来,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的“机动车体制”已然在中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形塑中产阶级对具体生活的理解。
实际上,私家车在中国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汽车虽于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但在1970年代末以前,政府禁止私人拥有私家车。直到1990年代,私家车才逐渐从公务用品转变为消费品。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私家车的普及和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相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轿车市场。
2004年,张珺和朋友在德国自驾旅行了一个月,德国人开车的习惯让她感觉很有趣:为什么德国产的车方向盘会很重,为什么德国会有不限速的高速公路?这其中包含着德国人对“速度”的理解:只有方向盘重,车才能开得快,因为开上高速后,方向盘很容易不受控制。
那么,中国人开车的习惯是怎样的,这些习惯指向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和社会观念?开车的习惯如何与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生活空间相互关联?这些好奇是张珺把博士论文选题范围定在中国私家车的动机之一。
出生在广州的她,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私家车从严禁个人所有的公务用品,逐渐转变为中产的日常消费品。从2006到2017年,张珺每年夏天都会回到珠三角地区跟进研究。张珺刚开始田野调查时,许多相熟的受访者渴望买车,其中有些是大学生,考驾照只是为了在简历中增添一笔。那时,张珺能盘点出市面上所有流行的车型,并且给出大致价格,“毕竟,车型总共只有寥寥几种,屈指可数。”从2010年开始,张珺的受访者中不少人成为车主,他们往往是自己家庭中第一代有车的人,而且他们第一次买的车大部分都是中等价位的中型轿车。
接下来,张珺见证了他们当中的小部分人的汽车升级,将一辆低端、袖珍型的小轿车(例如奇瑞QQ)升级迭代,换成中端的轿车(例如凯美瑞),甚至升级到高端的奥迪。多年来,她目睹不少人在买车方面受到的“同辈压力”,汽车不仅成为他们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必要出行工具,同时成为他们传递财富、地位或身份认同的媒介。
▲参观者在郑州车展上体验、选购私家车 图/视觉中国
张珺认为,私家车的普及表明,虽然轿车仍是确认个人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标志,但人们对于拥有轿车的愿望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工具性的,目的是获得社会地位”。随着轿车从只供少数人使用的专门物品转变为中产的日常用品,实际上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轿车生产成本的降低,轿车的重要性也已经随着它们所嵌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网络而演变。
“通过揭示轿车与中产阶级相互缠绕的关系,可以说明新的社会阶层有着怎样的面貌,并对传统上的‘改革开放’作一细致入微的描述。”她说。
持续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产”的概念也逐步进入张珺的视野。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产人士对其“中产”身份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跨国公司和媒体要在发展中国家开发新的消费群体,中国中产的言论曝光率大增。
在田野调查中,张珺的受访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中产”一词来谈论自己和某些生活方式。“中产”一词也透露出这些受访者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处于中间位置的感觉。张珺的受访者多是中年人,他们往往已经抵达职业生涯的中间点,也是多代家庭的中间层。使用“中产”时,他们将自己与新富们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精英,而认为自己只是通过努力工作谋生的“普通人”(或“一般人”),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
与此同时,张珺捕捉到了某种“焦虑”——这种既没有制度认证,又对未来缺乏清晰愿景的中间性导致了高度的焦虑感和脆弱性。因此,在“中产阶级”和“私家车”的交汇处,张珺探讨了中产阶级“如何感受轿车”,以及“如何通过轿车来感受”,并尝试透过个体的经验变化,把握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近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张珺,她的研究领域是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和空间政治、亚洲的科技与社会等。我们和她聊了汽车与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关系,人们对汽车的感知方式,以及交通工具的变化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带来的影响。
▲张珺 图/受访者提供
现代性是一种想象
南方人物周刊:“现代性”是你这本书的标题,也是主轴,在你基于汽车的研究中,“现代性”究竟指的是什么?
张珺:我在这本书里想讲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公路、汽车才是现代性,或者说更个体化的社会才是现代性。在我这里,“现代性”指的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一种感觉和向往。全球范围内的人都有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但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又是相当不一样的,怎样才算达到了现代性,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有很多学者强调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要用复数,即使不用也要知道现代性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我们在研究中,往往是抓住某时某刻某个具体的地方里的一种感知,或者说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经济力量的纠葛,从而形成的一种很独特的局面。我使用这个词时指向了更为主观性的层面。
南方人物周刊:从主观层面,人们对不同交通工具还是会进行比对,比如自行车和汽车,新世纪前后,开汽车可能会比骑自行车看起来更“现代”或者说“进步”?
张珺:我认为不能轻易地使用“进步”“落后”去解释。比如,到欧洲你会发现,他们的铁路网非常发达,很多人每天坐火车通勤。德国的私家车拥有率在世界范围内算是高的,但为什么火车的日常使用率也很高?包括你所提到的自行车,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同交通工具的选择同时存在。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在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工具是更好的选择,其实是跟很具体的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还有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2年,北京,市民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人们描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时,常会说到路上骑着自行车的人们。不同时间段会出现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交通工具吗?
张珺:大家以前会认为,出门自行车加上公交车就好了,因为那和我们的居住方式有关,在单位制体系下,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离得很近。在城市化之前,城市的面积和我们现在差得很远。以我成长的广州举例,当时的广州可能只是现在的中间一小块。从人口你也可以看到,1990年代初,广州市人口大概是600万左右,现在就超过1800万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在增长、城市面积在扩大,这一定会对出行方式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或者说是在城市规划的层面,我们会问:这个城市是为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而设计的?比如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广州市当市长,他提出,对于城市建设,道路发展是很重要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所讲到的道路,就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车为中心的交通设计。因此,“现代性是一种想象”这个问题,放在城市化建设里,就可以被转换成:你觉得一个现代的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在200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城市极速扩张的过程中,大家对城市的想象是道路就应该由汽车来主导。你会在很多城市的新区设计里看到多车道,特别宽的公路。
自由,还是便利?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私家车的兴起有历史的特殊性。1970年代之前,中国政府禁止个人拥有私家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国家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和交通网,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似乎会带来一些奇特的现象,也是中国在1970年代以前很少有“公路电影”的原因,而美国在1960年代就有“公路小说”或者“公路电影”。
张珺:在美国,公路片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公路、汽车的想象就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中产兴起是在战后,五六十年代,和学术界称的“郊区化”联系在一起,就是战后的白人中产(也涉及种族的问题)都往外逃,往郊区逃,觉得在郊区有车有房是一种理想生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公路片其实是以日常在郊区的生活为背景。公路是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强调一种“冒险”和刺激,在这里公路就成为了对未知的探索,也许有浪漫的偶遇,也有谋杀,它承载了与平淡的日常生活相反的想象。
而中国确实很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少数作为公务用品,轿车在总体上被看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它一直被压抑着。等到了1990年代,当时很多有名的学者在媒体讨论,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私家车,有人说会造成城市拥堵、有人说会造成阶层分化,但也有人说,有了车之后我们想出去玩会方便多了。之所以有讨论,就说明它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1990年代也可以说是过渡期,人们慢慢地开始接受轿车作为日常生活的用品,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塑的过程。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你在书中会特意提到大多数中国的中产在买车时考虑得更多的是“便利”而非“自由”?
张珺:如果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喜不喜欢自由,大概没有人会说不喜欢。但撇开这个概念,问他们为什么要买车,大家会自然而然地回答,“便利。”“便利”和“自由”有没有区别?可能有,但追问到最后会发现,区别可能也没那么大。美国人说自由,和中国人说便利,可能都指的是汽车可以让他们想去哪就去哪。也就是,他们的感受是相似的,但选择了不同的词来描述。当然,这个选择本身、对词语的使用习惯,背后也是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的问题。
▲兰州野生动物园内,游人自驾车辆在投喂区与野生动物互动拍照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购买汽车的中产阶级在日常使用中被“孝道”所束缚,他们要在个人欲望和家庭需求之间做出妥协,比如购买的私家车会成为一家人的工具。在这里面,怎么看待汽车本身的独立性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公私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张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独特现象,只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是中国问题,因此没有把其他国家放进去。在很多地方,汽车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的、独立的,它很多时候也是家庭用车。刚刚我们提到美国的“郊区化”,美国的郊区生活往往有两辆车,一辆是出去工作的人开的,大部分情况下是男性的车,而另一辆的车主一般是英文里说的soccer mom,这些住在郊区的中产家庭主妇,平时打扫家务、花很多时间带小孩儿去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去超市采购等等。美国专门会有针对这一群体的汽车广告,一般是七座商务车,所以这也是一种家庭需求。
可能在美国,大家觉得买这个车,哪怕问soccer mom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她可能还是觉得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车。但在中国,大家就很理所当然地承认这个车不纯粹是为我自己买的,这个车也是为了家人买的。实际上,他们在考量的过程中都把家人作为很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表述上很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私家车兴起的过程,也伴随着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过程,从集体经济式的、由国家统一安排的社会结构,转向了注重市场个体和社会流动的结构。私家车的兴起与“个体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珺:私家车的兴起,不仅仅是市场的选择,因为汽车工业可以带动上游的钢铁、煤矿等等产业,所以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利好选择。而在个体的层面,你又会发现社会在不断变化,城市在扩张,各种各样的需求在产生,汽车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必需品,所以这也是一环扣一环的过程。把汽车和个体化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汽车看作一种个体性的消费,或者是出于我自己对便利、自由的考量,但实际上这背后有着更宏观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变化等等。